我在餐厅里等我自己。咖啡是人造的垃圾,看起来像焦油,味道更差,但我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做,因为我的网络又出故障了。好吧,当时的景象是这样的:货船被推入码头,身后是一片闪闪发光的广阔空间。空间站停靠舱闪烁的灯光和缓慢爬行的移动看起来远比这家人造乙烯基内饰和格子地板的复古餐厅更吸引人。
码头的执法官和他们的灯塔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以至于我没有注意到另一个自己的到来;她滑进我对面的卡座,好像她一直在那里,在我的边缘,现在才成为焦点。
我们对视了一会儿。在餐厅明亮的荧光灯下,她看起来很疲惫,几乎憔悴不堪。她的皮肤像蜡一样。她眼睛下面有灰色的淤青。她的嘴被捏住了,好像她把所有的紧张都藏在紧闭的嘴唇后面。每天早上我在镜子里看到的那张熟悉的脸,已经被我未曾经历过的生活磨坏了。
“你收到我的留言了,”她说。
我点点头,放下咖啡。“已经有几年了。”
“当然。”
她把双手叠在叠层的桌面上,然后摊开。用长满老茧的拇指在指关节上摩擦。我抑制住了低头看自己的手,比较我们的伤疤和干净的角质层的冲动。“好吧,”她终于说,把手伸进工作服里,取出一个白色信封。
“嗯,”她又说。“我需要你帮忙。”然后她把信封从桌子对面滑过来。

阅读Nature Futures的更多科幻小说
我慢慢地把它捡起来。各种想法在我脑袋里乱转,但我想不出这是什么好意。钱吗?不——她在钻井平台上工作了很多年,必须赚很多钱。除非她把钱都赌光了我瞥了一眼她憔悴的脸,注意到她皮肤的黄色底色。药物吗?
当我终于把信拿出来并开始阅读时,我对自己之前不友好的猜测退缩了,尽管我被怀疑压在了原地。浏览到这一页的底部,我的注意力落在了那两行标志性的文字上。其中一个已经填好了。
我吃惊地抬头看着她。
她耸耸肩。“就像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一样,我似乎需要你的允许才能离开它。”
我喉咙里一阵发酸。我又低头看了看那封信。打印出来的文字模糊了,然后在我眨眼的时候又变得清晰了,我的眼睛突然因为迸发的情感而变得炽热。“医生协助自杀?”
“我生病了。别跟我说不明显,”她指着自己说。“显然器官衰竭在克隆人身上很常见。”
我依稀记得30多年前填写表格时曾提到过副作用。我是多么渴望创造一个能帮我还清债务的新生活。多么年轻和天真。
“对不起,”我对她说。“我应该……”
当我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她笑了,悲伤而短暂。“没关系。”
它不是。但这是我得到的最接近宽恕的东西。也许,在未来的岁月里,这足以减轻我知道我将会背负的一些罪恶感。
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笔,在写着“起源DNA”的那一行上签了名。我注意到,我们的签名完全不同。
“谢谢你,”她说着,把信塞回工作服里。
我们静静地坐着。我想说的所有事情与我刚刚签署的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什么也没说。我们本来不需要为此见面;她可以很容易地把文件发给我,并在几分钟内获得我的数字签名。不过,她也有自己的理由。我能从她的下巴上看出来。在我们周围,生活仍在继续:餐厅的门打开了,一群人进来了,他们的谈话和笑声充满了整个房间,就像膨胀的泡沫密封胶一样;在高压玻璃窗之外,黑暗的太空就在我们的指尖等待着我们,码头的指挥人员平静而精确地指挥着船只进入海湾。最后,另一个我点了点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不会再见到你了,是吗?”我抬头看着她说。
“大概不会。”
我有点想问问她的家人——如果她有家人,他们是否有办法在她去世后继续生存下去。但我可以从她冷静的眼神中看出,我没资格问。我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出于自私的原因。她根本不欠我什么。
换做是我,我会有不同的看法吗?
餐厅的门在她身后关上了,只剩下我一杯冰凉的咖啡和一种空虚的感觉在我的胸口。如果我是一个勇敢的女人,我可能会问她是否快乐,她的生活是否美好。如果值得的话。
如果我再勇敢一点,我可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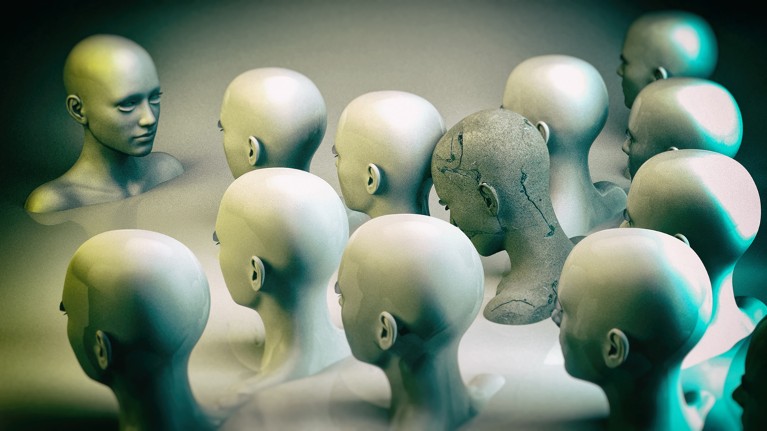
 马修·桑伯恩·史密斯著
马修·桑伯恩·史密斯著 地球化的心脏由M E加伯
地球化的心脏由M E加伯 你不能选择马特·泰的《纠缠
你不能选择马特·泰的《纠缠 像梦这样的装置是由马克·S·贝伦制造的
像梦这样的装置是由马克·S·贝伦制造的 霍尔·詹姆森的《逃犯》
霍尔·詹姆森的《逃犯》 黛博拉·沃克不高兴
黛博拉·沃克不高兴 J W阿姆斯特朗对哥白尼原理的更新
J W阿姆斯特朗对哥白尼原理的更新 让人类再次伟大!作者:Ian Stewart
让人类再次伟大!作者:Ian Stewart 《和我的人一起观鸟》作者:Sylvia Heike
《和我的人一起观鸟》作者:Sylvia Heike 检查你的口袋Robert Blasiak
检查你的口袋Robert Blasi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