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在我的指间轻轻拨动。
我觉得我也在敲击——就像那根针是我的延伸,我将永远是。这是这个嗡嗡作响的网络的唯一组成部分。每次我把针碰在屏幕上时,我的手都会产生微小的振动。我敢于仰望,我的目光闪烁,但我从不停止我的工作。还有无数排和我一样坐着的人,穿着同样的破衣服,向四面八方延伸。缝纫、缝纫。从那以后,每天都是一样的他们来了。
在我的屏幕后面有一根电线,拖下来,消失在前面的座位下面。成百上千的屏幕和电线相互连接。我坐在我那排的最后。498个座位。我知道我的号码;我知道我的位置。
往下一排,他们进入检查。右边的空气在颤抖。很快,我把目光牢牢地盯在我的工作上,我的手完美地移动着。我屏住呼吸,感觉空气在我脖子后面旋转,我把针划过屏幕,把两列字母连在一起。在A和t之间画两条线,在G和C之间画三条线.我的手颤抖了一秒钟,我感到颤抖的空气仍然在我身后。我耳边响起一阵轻轻的嘶嘶声。屏幕上仍是一字排开的字母。就是它了。这就是结局.我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做好准备。
它不来。

阅读Nature Futures的更多科幻小说
还有熟悉的喇叭声——刺耳刺耳。我们的屏幕变黑。我听见它在我身后后退。嗖的一声,它冲向了直线。空气在无形的存在周围融合和波动。动态实体。我松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我转向坐在我旁边的女孩。她试图给我一个微笑,她的脸因恐惧和疲惫而苍白。 I smile back weakly. The moment is fleeting. We must not be seen to be communicating.他们理解什么是沟通。
我颤抖着弯下腰,在座位下面抓住碗,然后把它拉到嘴唇上,感激地吞下尽可能多的肉汤。天气很冷。明天就轮到我们这一排人在大桶里做了。明天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把时间描绘成一条长长的黑线。现在我完全想象不出时间了。
喇叭又响了。我急忙把碗放在座位下面,我面前的屏幕亮了起来,迅速校准。那串字母又出现了,我继续做针线活。缝纫、缝纫。我画的每一条线都是一条缝。敲打,敲打。A与t, G与C.没完没了。我陷入了自我。我是穿针引线的针。
从我的左边传来一阵疯狂的哔哔声,大概离我20个人远。中间有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只要我的针从屏幕上抬起。然后有一种声音像呼啸的风一样他们来了。我不看,也不动。这种情况我见过无数次了。不匹配。大错特错。这名男子被从座位上扯了起来,飞到10米高的空中,然后被带走。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他只是在这里呆了一会儿,现在他走了。我继续我的缝纫工作。
*****
也许是一天之后。
喇叭响了。我转过身去看我旁边的女孩,然后像我记得的那样让自己停下来。她被抓走了。相反,一位老人坐在我旁边。他痛苦地伸手去拿他的肉汤,但他的手颤抖着把汤洒了出来。我迅速地握住他的手,自己把碗举起来递给他。
“谢谢,”他轻声说。我开始了,在沉默中呼吸了这么久。我点头回应,喝着自己的肉汤。
“你知道,我曾经是一名科学家,”他继续说,他的低语断断续续,嘶哑。我惊恐地听着他的话,准备感受空气中的变化。那人继续说,没有注意到。
“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也许这是人类的错,因为我们探索得太远,范围太广……某物会找到我们的。他们早在远处研究过我们,记住我的话。他们奴役了我们。你在屏幕上画的每一条线都是人工智能我们发明-翻译成DNA碱基之间的氢键。数据通过这些数不清的电线传输,同时形成了数百万个人类基因组。然后,他们将我们的DNA与他们的DNA混合,以实现他们最想要的…形式他的声音渐渐变小。
气氛有了变化。起初,有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微光。我振作起来。他们已经听见了。结束了.
相反,它们与我们擦肩而过。一行又一行的实体。不再是无形的。喇叭响了,是我们继续的信号。当我看到他们时,我的目光颤抖了。针在我手里颤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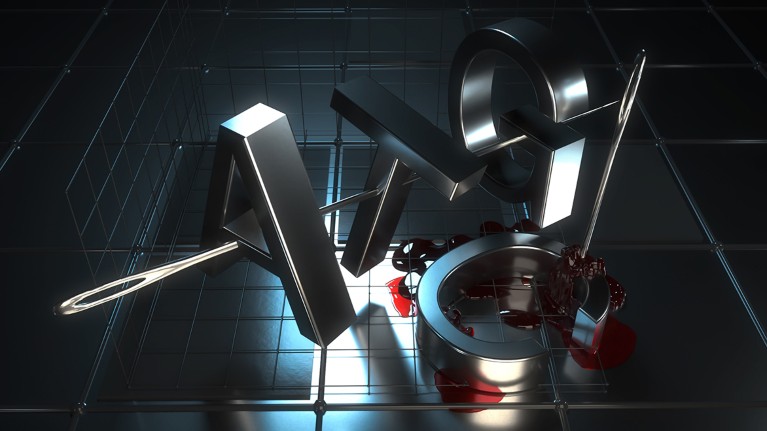
 《没有密码》作者:Marissa Lingen
《没有密码》作者:Marissa Lingen 杰夫·赫克特的“清晰空间基金会”
杰夫·赫克特的“清晰空间基金会” 贝丝·高德的遗言和小反叛
贝丝·高德的遗言和小反叛 艾米·皮基的《SS太阳之心》的紧急内务规则
艾米·皮基的《SS太阳之心》的紧急内务规则 贝丝·卡托分担痛苦
贝丝·卡托分担痛苦 阿尼夫陨石坑旅行图书馆的五本书,作者是斯图尔特·C·贝克
阿尼夫陨石坑旅行图书馆的五本书,作者是斯图尔特·C·贝克 《瓶子里的世界》作者:C·L·霍兰德
《瓶子里的世界》作者:C·L·霍兰德 休·卡特赖特的《如何矫正斑马》
休·卡特赖特的《如何矫正斑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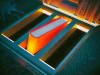 大卫·g·布莱克(David G. Blake)著,有些狗做梦时会踢
大卫·g·布莱克(David G. Blake)著,有些狗做梦时会踢 Peter S Drang的波函数归零
Peter S Drang的波函数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