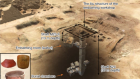18岁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满怀希望地离开了斯洛伐克,前往英国留学。我想利用我的父母在共产主义政权下成长时只能梦想的机会。但在我最疯狂的梦想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35岁之前成为一名教授。
我是靠体力和长时间工作才来到这里的。我狂热地工作以获得资助的博士和博士后职位。在一流大学的奖学金和职位的激烈竞争使我在早期教育和儿童发展领域的研究思路具体化。但为了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我把工作时间增加了一倍。对我来说,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时,一工作就是几个月,这并不罕见。
更多的工作时间意味着更多的成果。看到我对数字阅读的研究被转化成应用程序儿童或家庭网站激励我做更多的事情。我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常常以牺牲健康和社交生活为代价。

职业倦怠和冒名顶替综合症是如何影响科学事业的
我以为我是个例外。但当我读到一篇采访五位成功女性心理学研究者的文章时(p .亚历山大et al。建造。Psychol。牧师。33, 763 - 795;2021),我意识到这是表现最好的学者的标准。我非常钦佩受访者,并分享他们对工作的热情。但我现在意识到,以激情为借口,我是在为自己在研究领域的有毒倦怠文化做贡献找借口。对我和许多像我一样的人——女性、移民、非英语母语者——压力更大。是时候说出来了。
在我做临时博士后和讲师合同的那些年里,我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因为如果不多发表一篇论文,我就可能失去获得明年薪水所需的补助金。一位导师告诉我,进入学术界的通行证是出版物,所以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写作。医生告诉我冰可以缓解我的永久性腕管综合症,所以我戴着冰手腕夹板打字。
因为我的母语不是英语,所以每篇论文我都要多花几个小时。使用错误的词语而被误解的恐惧增加了会议演讲的压力,并转化为经常性的头痛和疲劳,我仍然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四个科学家花了一年的时间说不
表演的压力让我陷入了一个消极的漩涡。当我感到有压力时,我怀疑自己,害怕说“不”,对额外的任务说“是”来弥补,然后变得更有压力。我减少了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和睡觉的时间。我当时的男朋友告诉我,我嫁给了我的电脑,当他看到我在海滩上打字时,我们的假期缩短了。深夜通勤列车上的检票员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经常睡过头。当我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时,我的家人并不感到惊讶。
我现在明白了,我之所以选择努力工作,不仅是因为我对工作的热爱,还有一些系统因素。研究表明,年轻研究人员的倦怠风险更高(a·布恩et al。前面。Psychol。13, 839728;2022),以及来自边缘群体的女性学者,因为她们有更大的表现压力。尽管这也包括我,但我无法谈论影响许多年轻女性的更大压力,其中包括来自少数种族群体的女性,那些在母亲身份和早期职业研究之间挣扎的女性,那些来自LGBTQ社区的女性,以及来自存在极端性别歧视或暴力冲突国家的科学家。
通过努力和运气的结合,我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得到了一个长期职位。但随着我职业生涯的攀升,我的工作量只会越来越重,我越来越需要指导、文章和拨款审查、部门职责、委员会成员,以及自愿为专业协会贡献时间和专业知识。犯错误的成本也更高:如果我的低绩效耽误了一大笔拨款,可能会危及几个人的工资。

在科学中说“不”是不够的
但我的生存焦虑减轻了。组建家庭并移居挪威——一个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比英国更好而闻名的国家,这对她有所帮助。开始认真对待我儿时的爱好——写诗——是我为自己的心理健康做过的最好的事情。我也学会了更好地管理我的日程表,留出时间写作,也不会因为回复“不在办公室”的邮件而感到内疚。
我职业生涯早期的极端工作量对我不利,对其他人也不利。我想收回我对这种过度工作的有毒文化的贡献,尤其是对那些受到不成比例影响的群体。
我认为推广是我的责任学术成功的定义与极端的工作时间无关.在书中学术界的励志女性:支持职业生涯和改善少数族裔代表性(2023年),我的同事、伦敦大学学院职业发展主管洛丽塔·法哈德(Loleta Fahad)和我采访了女性学者和管理人员。我们公开分享我们失败的地方,我们希望在开始在大学工作时就知道的事情,以及当权者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系统性歧视。
对科学的追求让人充满热情:知识没有上限,发现的过程可能是全身心投入的。但对工作充满热情不应等同于加班加点。它不应该给来自边缘背景的女性带来额外的压力。


 职业倦怠和冒名顶替综合症是如何影响科学事业的
职业倦怠和冒名顶替综合症是如何影响科学事业的 为什么四个科学家花了一年的时间说不
为什么四个科学家花了一年的时间说不 在科学中说“不”是不够的
在科学中说“不”是不够的 压力和不确定性降低了研究生的满意度
压力和不确定性降低了研究生的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