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儿子hans Albert都追求卓越的职业在《科学》杂志上。来源:《南德意志报》除照片
孩子父母科学学位的两倍追求科学学位自己比父母华在其他领域(n Tilbrook和d . ShifrerSoc。科学。Res。103年,102654;2022年)。科学家的父母可以给孩子榜样,经常通过science-focused提供早期接触课外活动。孩子可以看到第一手的高点和低点的职业生涯在学术和工业研究发现,合作和机会到国外生活和工作。但这可以缓和强烈的工作负载发布临时合同,压力和时间远离家庭。
四位研究人员分享他们的父母如何影响他们的选择的研究事业和自己的父母影响了他们的科学。
弗雷德昌:尊重个人的选择和决定
细胞和组织的生物学教授,加州大学旧金山。
我父母从台湾移民到美国在1950年代追求研究生研究工程。我父亲大卫常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创办了一家公司在我们的车库,所以我的童年被电机和工具。我的母亲,海伦,当过职员科学家糖尿病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她把我介绍给一个生物医学实验室的环境和训练我去工作。我父母优先放在让我最好的教育,给了我机会来拓宽我的数学和科学教育。
在我30岁出头,我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我是细胞生物学家,我的前妻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所以我的女儿和儿子在家长大的音乐和科学。他们花了许多造型的夏天与我在科德角的树洞,我工作的地方是夏天研究员海洋生物实验室。树洞就像一个科学家、夏令营和我的孩子们看到我有多么有趣的发现,而与朋友和同事合作。
伍兹霍尔也运营着一个科学学院,我的孩子们学会了如何观察和探索丰富的自然环境在海边。他们现在在快30岁的时候。我的女儿一直着迷于地球的历史,和她现在的地质学家。我的儿子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喜欢建筑结构的可行性。
在我40岁,作为一名同性恋者,我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花了许多年;我认为我的未来是我最勇敢的行为。尽管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间每个人在家庭中,我们逐渐适应了变化。我的孩子已经支持的重要来源,他们完全支持我和我的伙伴。我想认为看到我浏览我的身份对我的孩子们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都有成长为冷酷无情,尊重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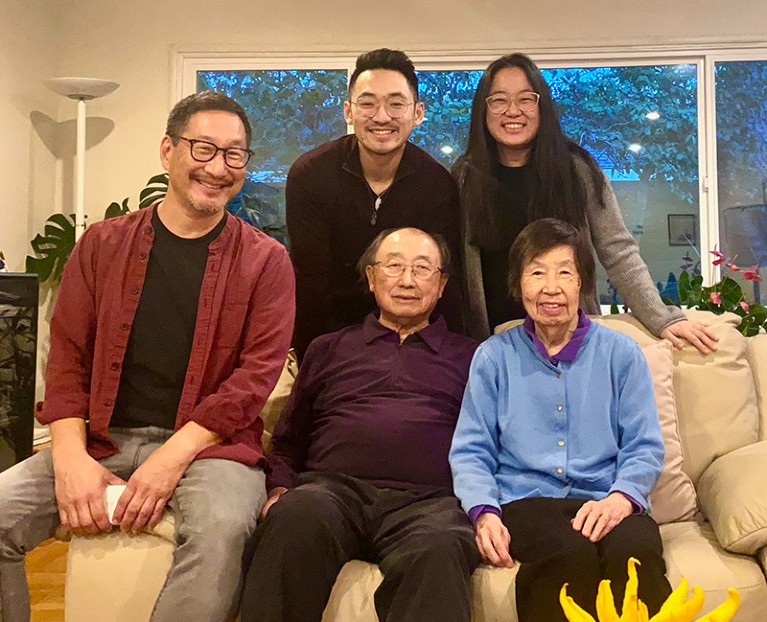
弗雷德昌(左)和他的父母和两个孩子。信贷:弗雷德常
乐天DE WINDE:学会划分和排序
研究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VU联电位置。
我的父亲是汉族de Winde生物技术在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员。我妈妈是一名儿科护士,为近25年的护士工作。她的名字是河南德Winde-van Zijl。当我出生时,我爸爸是追求博士学位,但即使他成为一个教授,他没有错过任何我生命中重要的时刻。他表明我可以平衡工作和生活,如何划分有助于实现这一点。我的学校假期期间,我曾经加入我的父亲在工作。我曾经为他添pipette-tip框,例如,我喜欢呆在实验室环境。之后,他带我去各种荷兰大学开放日,我们参加了医学和科学相关的项目和活动。
我最初想成为一名医生,但是作为一个大学生,我是深深吸引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研究。我想明白为什么一个系统,是由我们保持健康是未能根除癌症。现在,我学习淋巴瘤。我父亲读我的申请研究生院和给我建议就如何加强我个人的语句来表达我对研究的兴趣。我父母也鼓励我尝试我的手在许多事物。作为一个家长的一个1.5岁的女儿,我希望能够为她做同样的事情。

你是博士后在学术界或行业工作吗?分享你的职业经验与自然
我将完全支持我的女儿如果她选择类似的职业,因为研究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它对人好奇的心。但最重要如果是,我想让她做一些让她开心,无论是在科学或其他领域。
决定开始一个家庭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自2009年以来我和我的伙伴在一起,在2017年搬到英国。我们决定开始一个家庭在2020年之后才回到荷兰。我们觉得最好的工作安全,并接近我们的家庭。还有一个广泛接受的实践新父母工作四天在办公室或实验室在荷兰,这样他们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与孩子的早期生活。这些条件给我们的信心开始一个家庭。
为人父母教会了我一些宝贵的经验,我的工作中受益。我学会了我在工作和家庭角色划分。我曾经感到内疚,我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不能照顾我的孩子,但我也觉得我没有给我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后,我决定给我的研究在实验室当100%和100%时我的孩子在家里,它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的质量。
MARK PRAUSNITZ:生育与教授有相似之处
摄政的化学和生物分子工程学教授在亚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学院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我长大,我的父亲,约翰·普劳施尼化学工程师,现在是一个名誉教授。我的已故的母亲,苏珊•普劳施尼律师助理。很多朋友在他们的社交圈也研究人员。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给我和姐姐一个早期的科学的职业生涯会是什么样子。这种影响是通过软实力,关注人与科学的乐趣而不是硬技术内容在餐桌上讨论或作为解释世界的镜头。我妹妹成为医疗研究员和我决定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个化学工程师。

在研究和家庭生活:h从科学家爸爸诚实的反映
一个教训,我学会了从我的父亲被他的演讲题为《缩影化学工程和其他人文学科”,他在1990年代给了几次。虽然我已经是一名年轻的教授时,他给了这个讲座,他一直向我传达信息的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特别是,他解释了为什么科学研究人类努力,最终影响社会和社会如何反过来影响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我做的研究,这是适应工程技术来提高药物输送和其他医疗干预通过简单的,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改善病人的访问。
我作为一个工程师的培训工作影响我的指导风格以及我的父母在家里。工程经常强调效率和团队合作完成大型项目,和这种方法影响我运行我的实验室。我寻求优先活动需要参与和26个成员国之间的委托其他人我的研究小组。这种方法已经蔓延到我的生活和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公共卫生专业辛迪Weinbaum。我和我的妻子需要确定哪些活动我们会优先处理我们的孩子,和哪些我们可以委托,如穿梭他们年轻时和课外活动。
同样,作为父母也教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研究员。父母之间的相似之处和指导教授。我跑我的实验室作为一个导师,而不是一个老板。我指导我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提供建议(有不同程度的紧迫性),帮助他们成为独立的研究人员。这种指导风格也反映在我的父母,和我看到自己指导自己的孩子独立,。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看到我的孩子和我的实验室成员成长,继续做出自己的对人类的影响。

与她的伴侣瓦莱丽·杨上,亚历山大狂吠,和儿子。信贷:燕Jiejun
瓦莱丽·杨上:纪律和选择什么是正确的
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助理教授。
我记得一个故事来自一个同事把著名的教授退休派对。邀请加入的时候,他的孩子们说,他们不想参加宴会,因为他们的父亲专用的那么多的时间,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工作,他是一个父亲。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提醒我不要进一步我的事业牺牲我的家人。

科学家面临的教育惩罚的母亲
我的父亲约瑟夫·杨,我的母亲,特蕾莎狂吠,全科医生,所以成为一名医生是一个自然的职业生涯的决定。然而,我爸爸常常鼓励我去科研、告诉我故事的医疗实践的局限性。例如,他描述了如何将实验结合不同的现成的面霜来实现最好的结果顽固的湿疹患者,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病人的表现好于其它地区。最终,我折中,开始攻读肿瘤学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2006年英国。
我儿子在2016年,在我临床专业培训,并获得了我的第一个独立格兰特的前一天我生了,所以不得不提供婴儿和研究。经过三个月的产假,我回去工作,我看到了我儿子的一些重要的里程碑,例如独立坐起来,滚,牙牙学语,第一次尝试不同的食物。我5点前离开工作,直到过去的11点才返回。一夜之间,经常不得不呆在医院病房或重症监护室覆盖率随叫随到。所以我决定把六个月的无薪假期,这样我就可以花费质量时间与我的儿子。肯定觉得我是我职业生涯危害通过推迟退出考试对我的临床专业,但我现在知道,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不能让时光倒流,见证我儿子的里程碑,否则我会错过,但总会有其他赠款和我发展我的职业生涯的机会。
父母教会我更为严格的在我的工作和奉献我的时间和有限的资源项目,真正最重要的给我。

 First-in-family学者破产世代壁垒
First-in-family学者破产世代壁垒 弱势背景不一定是成功的一个障碍
弱势背景不一定是成功的一个障碍 大流行性流感措施不成比例的伤害女性的职业
大流行性流感措施不成比例的伤害女性的职业 你是博士后在学术界或行业工作吗?分享你的职业经验与自然
你是博士后在学术界或行业工作吗?分享你的职业经验与自然 在科学事业和家庭生活
在科学事业和家庭生活



